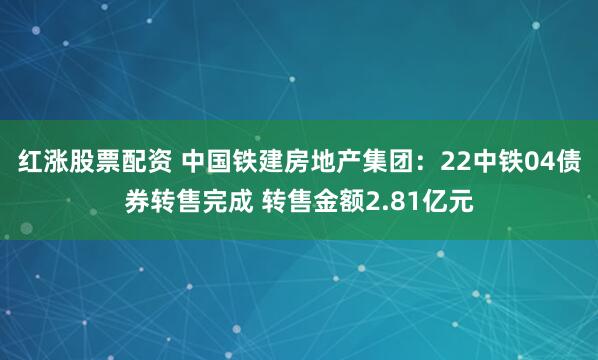此文前一鼎盈,诚邀您点击一下“关注”按钮,方便以后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新的文章,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动力~

文|避寒
编辑|避寒
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英格兰修道院的腐败早已烂到骨子里,不是一两个神职人员的堕落,而是整个制度的失控。

女院长和男牧师公开苟合,主教多次干预都失败而归,不是他不想管,是压根管不了。
到底哪里出了问题?真相藏在700年前的英格兰修道院里,一层层剥开,才发现,所谓“禁欲清贫”,只是面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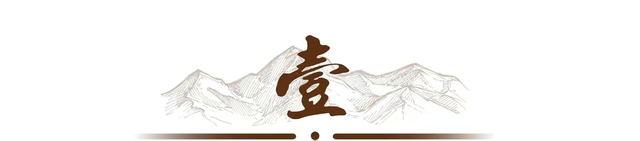
宗教外壳下的堕落温床
中世纪的英格兰,宗教不是信仰,是产业。“修道”这件事,本是为了清心寡欲,实际却成了逃避世俗责任的遮羞布。
进入修道院,不光能躲避婚姻,还能免税、免兵役、享土地。对一些贵族家庭来说,把多余的女儿送进修女院,是经济安排。对下层家庭来说,成为修士,是翻身的唯一机会。

修女院一度是贵族女子的养老院,是二女儿的退路,是贵族政治的延伸。她们带着嫁妆、封地、仆人进院,哪像什么“出世”?根本是另一个宫廷。
七世纪起,本笃会传入英格兰,强调遵守“贫穷、贞洁、服从”的三大誓言。但这三句承诺,到十四世纪,几乎成了笑话。
十四世纪中叶的英格兰,修道院已是遍地铺开,表面神圣,内里烂透。学术凋敝,管理崩坏,贪婪无底,最关键是:没人能查,没人敢管。
英格兰宗教体系的最大漏洞,在于监督。当时主教对修道院有名义管理权,但每个教区主教要监管上百家修道机构,查不过来;而罗马教廷远在欧洲大陆,鞭长莫及。
你以为修女院清苦?错,许多修道院附带土地、酒庄、工坊,每年收入上千英镑,堪比小侯爵府。修士修女成了地主,自己不种地,却抽税、租地、收捐献。

1348年,瘟疫袭来,黑死病席卷英国,城市凋敝,乡村荒废。但教会却没垮,相反,大量土地因主人病亡转入教会手中,修道院趁机扩张,几乎是“瘟疫赢家”。
可问题也在这时彻底爆发了。大批修士死于疫病,经验断代一鼎盈,剩下的新任院长和修女,大多素质低下。许多女院长不识拉丁文、不懂会计簿、甚至不守誓言,靠裙带关系上位。
当制度依赖“自律”维持时,最先崩的是人性。

女院长、男牧师、和形同虚设的主教
修道院的权力,不在神,而在女院长。
根据《本笃会规》,女院长年满40岁、修道10年以上,方可竞选。听上去严格?实际上,很多修女未满十年就“被加速”,背后是贵族势力运作。尤其是像林肯、诺里奇这类大院,女院长就是该地地主贵族的“代理人”。

在十四世纪,多个调查记录表明,一些女院长公然与牧师同居,有的甚至在院内设专门“男客房”,常驻两三名青年神父。
1349年,《坎特伯雷教区年鉴》记载一起事件:某修女院中,女院长与驻院神父“关系亲密”,夜间频繁互访,导致其他修女多次抗议,最终三人怀孕,主教派人调查,女院长拒不承认,还命修女闭口不谈。
主教能查吗?能,但主教自己也有麻烦。他每年从修道院拿“赞助费”,多的上百英镑,收钱又要查人,哪有底气?
更何况,许多主教本人也有秘密情妇,甚至有的干脆在别处修建“行宫”,他们怎么可能正面刚?
主教的调查报告往往被束之高阁,或者干脆由罗马驳回,因为修道院上交的钱太多,没人敢真的动。

一份诺丁汉主教写给大主教的信件中提到:“某女院长长年与男牧师共居,有修女向我检举,被其锁入地牢,现人已疯。”这封信被发现时,已过去五年,院长依然在职。
到底谁该负责?谁有权力?谁愿意承担后果?
没人。
教会自己没能力惩戒,国王也不敢得罪教会,平民只敢私下嘲讽修士的肥肚和修女的香水味,没人敢举报,更没人能真正制裁。
而在许多地方,修道院还承担着医疗、教育和施舍的角色,它腐败归腐败,却又是地方社会的支柱。砸它,就等于砸平民的命根。

在这样的悖论下,一个女院长和男牧师的苟合,不过是冰山一角,更深的,是整个制度的放任与合谋。
不是主教不想管,是他被困在制度泥潭里,动一根藤,满网乱颤。
 一鼎盈
一鼎盈
修道院的脸烂了,制度还在涂粉
十四世纪的英格兰修道院,看上去还是那副“圣洁高墙、钟声悠扬”的样子,可一进门,才知烂得透透的。
最先烂的,是修道誓言。
所谓“清贫、贞洁、服从”,在现实里变成了“聚财、淫乱、专断”。

1348年,坎特伯雷主教托马斯·布拉德沃德因“接到太多关于修道院丑行的投诉”,不得不派出主教代表团,对16家修道机构进行走访。结果骇人:
一家修女院中,有四名修女怀孕,两名已秘密分娩,婴儿被送往村庄寄养;
某修士每天饮酒三升,院内藏有“舞会服饰、木笛、棋盘”等娱乐物品;
一名院长私设地牢,将抗命修女关押超过40天,事后还夺其财物。
而这些只是冰山一角,真正的“日常腐败”早就渗进血液。吃喝玩乐成风,祷告成了摆拍,修道变成权力游戏。
经济上,修道院已成为“地主集团”。土地、租金、农场、磨坊,全是收入来源。问题出在哪?出在“没人看账”。
修道院的财务,一人记账,一人审批,全靠“修士自觉”,但自觉从来靠不住。

1349年,约克城一间修道院账本中赫然写着:“用于女院长卧室织毯六金镑”“支付男仆治病药草三银镑”,男仆?织毯?对不起,那些钱是老百姓捐的,是赎罪钱。
更荒唐的,是“售卖赎罪”。所谓赎罪券,本该是一种宗教仪式象征。但十四世纪起,修道院公开设柜台出售,“三便士免一日炼狱,六便士清洗三月罪行”。
信仰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,穷人卖地赎罪,富人一掷千金换“天堂门票”。
当时有学者记录一幕:某男在忏悔室里坦白与修女通奸,忏悔师却让他“捐一笔银币为她祷告”,这不是宗教,是性交易外带附赠礼金。
而管理呢?谁来查账?谁来纠偏?没人。
即便主教派人来查,也查不动。修道院往往“提前通知”,准备好账本、清空房间,找几个忠诚修士背台词。

外人来了,院长一派虔诚,修士规规矩矩,书房整洁,祷告井然。主教一走,门一关,又是一锅烂肉翻炒。
当时流行一句民谚:“修道院白日念经,夜里饮酒跳舞。”讽刺得狠,也说得真。

腐败被记住了,但改革来得太晚
英格兰的教会不是没人想改,改不动。
早在十世纪末,盎格鲁-撒克逊王国时期,曾有一波“回归本笃规”的运动。主张清除世俗神职、重建修道生活、落实独身禁欲。

但随着贵族渗透,改革失败,为什么?修道院的经济利益太大,没人真想放弃。
十四世纪,各地的“教会访查”报告越来越多。投诉信件中,关键词集中在“淫乱”“贪婪”“打人”“贿赂”,已非个别行为,而是制度化腐败。
可王权也不愿碰这个马蜂窝。
直到两百年后,亨利八世上台,为了摆脱罗马教廷控制,又要夺回修道院巨额土地,他干脆一口气查抄了800多座修道院,彻底砸了这个千年制度。
不是因为信仰变了,而是利益重分。
但砸归砸,那些修道院留下的东西,至今还在。

比如图书馆。许多修道院在乱世中反而保住了珍贵文献。像《盎格鲁-撒克逊编年史》《主教登记薄》都是在十四世纪修院中保存下来的。
这也是讽刺:一边藏书万卷,一边教义腐烂。
历史学者们通过这些账本、调查报告、赎罪券记录,还原出那个荒唐时代的真实图景。不是凭空想象,而是有笔有字、有章有据。
就连讽刺诗也没放过修道院:“修士腰缠银器,修女绣花丝衣,神像哭泣不止,说我本不想住这屋。”
荒唐又真实。

700年前的英格兰修道院,不是宗教殿堂,是权力和欲望妥协后的产物。那些女院长、男牧师的丑闻,不是道德沦丧的个案,而是结构性腐败的必然。
谁管不了?主教管不了,国王不愿管,信徒无力管,直到制度自己崩塌,才算落幕。
可这一切一鼎盈,真的结束了吗?
稳赢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